中国翻译家沙博理
来源:
《礼记?中庸》有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文心雕龙?事类》有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他本是犹太裔美国人,名叫Sidney Shapiro,同学为他取名“沙博理”,意思是“博学明理”,“沙”是英文姓的音译。青年时期他背井离乡来到中国,人到中年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人。因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他选择翻译为一生的事业,又因为翻译他的“中国情怀”愈加浓厚。他将半生奉献给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事业,这一切都源于那张美国面孔下的“中国心”。
第一节 此处安心是吾乡
1915年12月23日,沙博理出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位律师。幼年的沙博理家境宽裕,在父母的关怀下度过愉快的童年。1937年,他从圣约翰法学院毕业,随即子承父业成为一名律师。然而,喜爱冒险的沙博理对纽约的律师界产生了深深地厌倦。同时,各种打着公正旗号的黑暗交易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他的良心。年轻的沙博理一直等待着生活的转折。
终于在机会来了。1941年,沙博理二战入伍,被派往康奈尔大学学习一门外语,在那里他偶然结识了中文,开始对这门古老而又精深的语言产生了兴趣,从而也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心生向往。1946 沙博理退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注册学习两个学期中文,第三个学期转入耶鲁大学学习。1947年,沙博理决定亲自前往中国。3月,他只身一人带着很少的旅费,坐上了前往上海的油轮,经过一个月的颠簸才抵达上海。
来到中国后,沙博理结识了中国戏剧家妻子封凤子,两人最初只是互教对方英语和汉语,渐渐地凤子身上体现出的独立、勇敢、文雅的气质深深吸引了沙博理,两颗心自然越来越近。1948年5月16日,沙博理与凤子喜结连理,从此决心定居中国,这时他的身份是一名在上海工作的美国律师。妻子凤子是沙博理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一扇窗口,凤子出身于书香门第,曾就读于复旦大学,作为戏剧演员文化底蕴深厚,任何沙博理学习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都能给予解答。沙博理晚年在自己的自传里写到:“凤子不仅是我的妻子,也是我与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爱上了凤,也爱上了龙,了解和热爱中国龙,使我更加热爱和珍惜我的中国凤。”(沙博理、宋蜀碧,1998:443)
1948年,沙博理与凤子参与了上海的共产主义运动,11月他们跟随地下党人士移居北平解放区,从此定居北平,而这一住就是六十多年。经朋友介绍,沙博理被对外文化联络局聘用,成为一名专职翻译工作者。1953年,沙博理开始在中国外文局工作,担任《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杂志社的翻译、改稿员。为了更安心地在中国生活工作,1963年,沙博理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加入中国国籍。1972年,沙博理转入外文局的《中国画报》杂志社,继续从事汉英翻译工作。1983年,退休后的沙博理被任命为第六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分配在全国政协的新闻出版委员会,并一直连任至今。在此期间,他曾就中国社会的方面问题递交提案,以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国家做出贡献。
五十多年的翻译生涯中,沙博理翻译中国经典著作达千万余字,可谓译作等身,其中大多质量上乘。他的译作题材丰富多样,既有中国古典名著、民间故事集、近代红色文学作品,又有现当代文学作品,体裁囊括小说、散文和诗歌等。其中的代表有:《新儿女英雄传》(Daughters and Sons, 1956)、《家》(The Family,1958)、《林海雪原》(Tracks in the Snowy Forest,1962)、《水浒传》(Outlaws of the Marsh,1980)、《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Deng Xiaoping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A Daughter Recalls the Critical Years,2002)等。具有犹太血统和律师背景的沙博理,还利用退休后的时间,通过亲身调查研究编译了三部学术专著,分别是:《中国古代犹太人》(Jews in Old China: Studies by Chinese Scholars,1984),《中国古代刑法与案例传说》(The Law and the Lore of China’s Criminal Justice,1988),《中国文学集锦:从明代到毛泽东时代》(A Sampler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Ming Dynasty to Mao Zedong, 1996),引起了国际同领域专家的广泛关注。除此之外,沙博理也曾尝试独立写作,包括两本自传《一个美国人在中国》(An American in China, 1979)和《我的中国》(My China: The Metamorphosis of a Country and a Man, 1997)。任政协委员期间,他曾就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事业提出过多项提案,包括“发挥文学在文化宣传中的作用” (2009),以及“让中国文化走出去”(2010)等。由于戏剧家妻子凤子的推荐,沙博理还曾在《西安事变》《鹰击长空》等国产电影中客串过角色。如今,百岁的沙博理仍然笔耕不辍,时刻心系中国的社会发展,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贡献力量。
半个多世纪的对外文化传播事业,也为沙博理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与殊荣。1994年,沙博理被中国作家协会授予“中美文化交流奖”。① 1995年1月,中华全国文学基金会及中国作家协会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授予沙博理“彩虹翻译奖”。② 2003 沙博理被推选为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③ 2009年9月4日,被中国外文局授予“国际传播终身荣誉奖”。④ 同年11月14日,“中国因你而美丽”——《泊客中国》2009颁奖典礼上,沙博理作为国际友人获奖。⑤ 2010年12月2日,沙博理被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⑥ 2011年4月2日,在“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2010-2011”中,沙博理最终荣膺2010-2011年度“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⑦
2014年10月18日,沙博理于北京的家中溘然长逝,享年99岁。
第二节 半个世纪的翻译生涯
自1951年,沙博理开始在对外文化联络局担任专职翻译。1953年起,他作为外国专家,与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等在外文出版社的《中国文学》杂志社从事汉英翻译工作。1972年,沙博理转入外文出版社的《中国画报》杂志社,继续从事中国文学作品的汉英翻译、编辑工作。沙博理所供职的外文出版社隶属于中央直属的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负责对外宣传报道和出版,因此他是一名“国家翻译机构的”受聘译者,翻译行为会受到国家翻译政策的影响。1983年,退休后的沙博理成为了一名自由译者和作家,他的翻译活动具有了更多自由性。纵观沙博理一生的翻译生涯,很大程度上与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阶段相一致,因此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新中国十七年时期(1949-196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全国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中国的翻译事业也亟待规范化。“尽管在这个刚刚创建的国家中,官方化的翻译活动并不十分稳定,然而由国家和党政机构逐渐代替各种私人活动这一整体趋势从未改变。”(滕梅,2008:69)政府机构直接介入,大政方针的指导,系统化都是这个时期翻译活动的特点。(魏瑾,2009:31)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苏联人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m realism)学说成为了一项政策,作为一种权威的意识形态指导着包括翻译在内的各种文学艺术领域。文学翻译的首要任务成了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即“保卫和建设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主题上无外乎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资本主义”(刘彬,2010)
外文局下属的外文出版社是这一时期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阵地,而《中国文学》是译作传播的唯一官方载体。此时新中国对外译介的大都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题材的当代作品。对外翻译工作可分为四步:1.中国学者选择需要翻译的作品2.中国译者翻译这些作品3.外国专家对翻译进行校对 4.官方专家对译作进行定稿。(徐慎贵,耿强2010)沙博理作为一位中籍美裔译者,不仅是“外国专家”也是“中国译者”。
新中国十七年时期可谓沙博理翻译生涯的“高峰期”。(任东升、张静 2011)从1951年到1966年,共有111部文学作品的124篇署名沙博理或匿名的译文刊登在《中国文学》上,共计3237页。(江昊杰 2014:34)2011年5月31日,沙博理做客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时曾用“红色中国文学”来指代自己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黄玉琦,2011)其中大部分的译文又以英文小说的形式由外文出版社发行。根据内容我们将其归纳为三类:
(一)反映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小说,如:《铜墙铁壁》(Wall of Bronze ,1954)《平原烈火》(The Plains are Ablaze ,1955)《新儿女英雄传》(Daughters and Sons ,1956)《保卫延安》(Defend Yenan!,1958)《小城春秋》(Annals of a Provincial Town ,1959)等;还有东北地区人民解放军镇压土匪的小说,如《林海雪原》(Tracks in the Snowy Forest ,1962)等。
(二)批判封建官僚主义,反应解放战争后阶级斗争的小说,如《李有才板话及其他》(Rhymes of Li Yu-tsai and Other Stories ,1951)《柳堡的故事》(It happened at Willow Castle ,1951)《活人塘》(Living Hell,1955)《春蚕集》(Spring Silkworms and Other Stories ,1956)《家》(The Family ,1958)等。
(三)展现新中国建设、赞扬劳动人民的小说,如:《农村散记》(Village Sketches ,1957)《创业史》(Builders of a New Life ,1964)等;另外沙博理还翻译了评剧《夫妻之间》(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A Play in One Act 1953),连环画册《巧媳妇》(Mistress Clever, 1954)以及一本政治诗歌《酱油和对虾》(Soy Sauce and Prawns, 1963)等。
抗战和解放战争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亟待提高,外文局选译的作品内容上都是为树立新中国对外形象而服务的。国家翻译机构对于受聘译者有政策上的要求,但译者仍有自由发挥的空间。沙博理这段时期的译作内容题材丰富多样,但语言转换能力方面略显稚嫩,文化因素的传递上也尚有不足。
二、文革“十年”时期(1966-1976)
此时期中国的翻译事业陷入低谷,外文出版社的正常运作也一度受到干扰。对外文学翻译以汉语为出发点,旨在通过文学作品的输出“对外传播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世界革命”(李晶,2008:52),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并且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作了文革政治的传话筒”(田文文,2009:20)。这一时期国家机构介入到了翻译的每一个过程,包括选题、指定译者、翻译原则和策略的制定、甚至出版发行。政治考量在很大程度上高于文学翻译原则本身。因此,译者的独立性或多或少遭到了剥夺。
此阶段沙博理既作为专职翻译家独立承担文学作品的翻译,又作为外国专家参与译作的校对和润色,可以说身兼数职。文革时期以集体合作翻译和匿名翻译为主,因此沙博理公开译作数量不多,其间最后一篇署名的英译作品为《欧阳海之歌》(The Song of Ouyang Hai ,1966)。然而他一生中最具影响力的译作于此间诞生——1980年出版的《水浒传》译本Outlaws of the Marsh。这本书的书名翻译甚至曾让他卷入一场与“四人帮”的政治较量中。最初这本书被译为的Heroes of the Marsh,然而“四人帮”不认可对梁山好汉Heroes(英雄)的称呼。沙博理机智地将“heroes”改为“outlaws”。outlaw本意为无法无天的人,实际上在西方文化中有着“劫富济贫的民间英雄”这层含义。(沙博理 1984)如此一来把“四人帮”蒙骗了过去。此外,他还作为外国专家参与毛泽东诗词英译稿的润色和讨论。其间他提出没有注释的手稿不利于外国读者准确理解欣赏毛泽东的诗歌,也引起过江青的不满。(马祖毅 2007:221)
三、新时期二十六年(1976-2002)
这一时期,尤其是1983年退休后,沙博理逐渐由国家翻译机构受聘译者转变为独立译者和作者。出版的著作有:《一个美国人在中国》(An American in China, 1979)、《四川的经济改革》(Experiment in Sichuan: a Report on Economic Reform, 1981)、《马海德:美国医生乔治?哈特姆在中国的传奇》(Ma Haide: The Saga of American Doctor George Hatem in China, 1993)、《我的中国》(My China: The Metamorphosis of a Country and a Man, 1997)等,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此同时,他先后整理、编译《中国古代犹太人》(Jews in Old China: Studies by Chinese Scholars,1984),《中国古代刑法与案例传说》(The Law and the Lore of China’s Criminal Justice,1988),《中国文学集锦:从明代到毛泽东时代》(A Sampler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Ming Dynasty to Mao Zedong, 1996) 3部书。另外沙博理还翻译了一些短篇小说,包括《湖畔儿语》(The Child at the Lakeside)、《春桃》(Big Sister Liu)等,收录于《中国现代名家短篇小说选》(Masterpieces by Modern Chinese Fiction Writers, 2003)。此时期中沙博理最重要的翻译作品应属《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Deng Xiaoping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A Daughter Recalls the Critical Years,2002)。此书作者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专门指定沙博理代为翻译。而他的翻译也显现出极大的译者主体性,通过选择作品、撰写序跋和专文、操纵文本等方式对外推介新时期文学。
第三节 代表译著
沙博理专事中国文学作品汉译英事业近五十余年,总翻译字数达千万,其中许多译文是原作品译介到西方的唯一版本,为中国文学翻译及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鉴于他的译作众多,我们分别从他翻译生涯的三个阶段选取代表性译作的加以介绍点评。
一、《新儿女英雄传》(Daughters and Sons, 1956)
建国后十七年间,大批“红色”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以电影、戏剧、连环画等艺术形式得到广泛传播。“红色小说”即“革命历史小说”,“专指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创作的,以1921年中共建党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为题材的小说”。(黄子平 2001:20)红色小说最能代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成就,此时期国家对外翻译的主要题材也以红色小说为主,目的是为了“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树立新中国的良好形象”。(王晓燕 2012:30)沙博理为革命历史小说的对外英译曾做出巨大贡献,就职于《中国文学》杂志社期间,他所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基本都可归于这一类。沙博理本人十分喜欢翻译这些小说,他“对其中的许多人物感到亲切。中国的男女英雄都有那么一股勇气和闯劲,强烈地使人联想到美国的拓荒精神”。(沙博理 宋蜀碧 1998:118)
《新儿女英雄传》不仅是沙博理翻译的第一部中国小说,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小说。此书中文作者袁静、孔厥,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冀南白洋淀以主人公牛大水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共产党员与日军游击作战的英勇事迹。1951年这本书的英译Daughters and Sons刊登在当时国内唯一的官方文学对外翻译机构外文出版社所属的《中国文学》第一期上。1952年,由美国自由图书俱乐部在美国出版,1956年由外文出版社在中国正式出版。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文学创作批评的最高标准在整个中国盛行。这一时期的作家创作要力求准确再现历史,以深刻洞察力反映社会现实。英雄人物题材最能激发读者的共鸣,因而成了突出这种诗学的主题。此时的对外的翻译活动也主要选取刻画爱国英雄的作品,并着重在翻译中渲染英雄事迹。作为国家翻译机构中国外文出版社的译者,沙博理对这一翻译目的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体现在他不同的翻译策略中。具体策略主要有:
(一)译著前言的政治考量
通常来说,译著前言的主要功能是对作者和整部作品进行评价,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整部作品。通过仔细分析《新儿女英雄传》译本前言,我们能发现译者贯穿整个翻译过程的目的和指导思想。
《儿女英雄传》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一群中国青年儿女游击抗战的故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紧紧跟随党的政策方针,与各阶层群众团结一致,在华北地区敌军后方艰苦作战达八年之久,而这期间国民党军力屡屡溃败。他们紧密联系人民群众,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他们还开辟新战场,增强军力,克服千难万险,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贡献卓著。(笔者译)
在这份前言里,沙博理着重从政治视角突出介绍共产党员及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操和英雄主义精神,批判国民党的作战不利,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点恰好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符。除此之外,译者没有增添任何无关主题的主观见解。
(二)突出具化英雄人物的优点
为了突出抗日英雄英勇抗战的大无畏精神,沙博理在译文多处做了增译及具化处理。如:
【例1】 “老蔡,你不用动员我!我接受党交给我的任务,一定想办法完成它,你放心吧!”(袁静、孔厥 2005:19)
“You don’t have to ‘rouse’ me, Blacky,”he growled. “I know how to accept a Party responsibility. If I die, it’ll be with honour.” (Shapiro, 1956:178)
例1 描写了主人公牛大水英雄气概及革命责任感,沙博理为了进一步突出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以及对党的热爱,添加了“If I die, it’ll be with honour.”使原意得意更加完整地传达,人物品质更加生动。
(三)简化省译英雄人物的缺点
对于英雄人物形象中缺点的刻画,沙博理有时会采用简化甚至省略的翻译策略,将人物性格和行为不好的一面淡化,从而让读者眼中的英雄人物更加完美。其中最多的是原文中主人公的粗话,如“妈的”“狗娘养的”等等,都被沙博理省去不译。再如:
【例2】 一会儿,一家人都起来了,忙着烧水做饭。申耀宗给牛大水钥洗脸水、漱口水。大水说:“你快洗了走吧。我也没有牙刷牙粉,随便洗洗就得了。(袁静、孔厥 2005:159)
Before long the whole family was awake and busily preparing breakfast. Shen brought water so that his guest could wash and rinse his mouth.
“You wash first and go, quickly,” Ta-shui directed. (Shapiro, 1958:186)
原文最后一句中的“我也没有牙刷牙粉,随便洗洗就得了。”沙博理完全从译文中省略。因为主人公牛大水不在乎个人卫生的这一行为有损于他在小说中的英雄形象。
另外在处理原文中带有“红色”印记的文化负载词,沙博理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既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中国文化意象,准确传达文化词内涵,又兼顾了外国读者的阅读需求,提高文本接受度。
贯穿沙博理整个翻译过程的指导思想是突出原著时代背景下的政治意义,正确反映原作者真实意图,对外树立新中国崭新形象,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他采取了各种灵活的翻译策略。诚然,作为沙博理的第一本译作,Daughters and Sons并非十全十美。第一次尝试翻译中国小说的沙博理中英文水平都尚未达到十分高超的水平,译文难免存在不足。但1952年这部小说成功在美国发行,为国家规模的中国文学对外传播开了个好头。这部成功译介的作品更为后来的其他文学作品的翻译提供了可借鉴的翻译模式。从那以后,沙博理和他的同事们陆续译出新作品,中国文学传播事业势头良好。
二、《水浒传》的英译(Outlaw of the Marsh,1980)
Outlaws of the Marshs是沙博理最有影响力的译作,代表了他翻译生涯的最高水平。他的《水浒传》译本不仅赢得中国文联授予的最高翻译奖,2000年还作为最权威的英文版本,被收录到外文出版社编辑的《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从而具有“建构中国英语的语言表达相对规范的形式和确立中国英语独立地位的基础”的重任。(傅惠生 2012)
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讲述了北宋末年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位将士英勇起义的故事。几百年来这部章回体小说不仅在中华大地家喻户晓,也通过其多语译介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水浒传》的英译本已先后有四部问世,包括:赛珍珠(Pearl S.B.)的All Men are Brothers(1933)、杰克逊(Jackson J.H.)的Water Margin(1963)、沙博理的Outlaw of the Marsh(1980)、登特杨父子(John Dent-Young, Alex Dent-Young)的The Marshes of Mount Liang(1994)。其中沙译本以其准确的理解,流畅的语言和文化因素的巧妙传达赢得了众多读者和学者的一致好评。美国汉学家西里尔?伯奇(Cyril Birch)在《威尔逊季刊》上评价道:“赛珍珠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将《水浒传》部分地带给了西方,但是沙博理努力的成就要优秀三倍。他的中文知识使这个译本更加准确;他的直截了当的易懂的英文,证明比赛珍珠模仿中国古文的难懂的话更加优美得体;它依据原著较早的版本,出版了更加完整的作品……”(沙博理,1998: 322)
沙博理翻译水浒传时正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此时国家意识形态凌驾于所有文化艺术活动之上,中国的翻译事业受到明显的政治因素的操控。沙博理作为外文出版社译者的政治身份在这一时期也最为凸显。在翻译《水浒传》的过程中,其译者的主体性受到很大程度地限制。首先,《水浒传》的翻译初衷也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当时毛泽东借《水浒传》,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引起了对这本小说的热议,“四人帮”借机夸大。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水浒传》被要求重译为英文。这项工作不仅是一项翻译任务,还具有政治革命意义。赞助人不仅能够推动他们支持的翻译项目,还能有力地阻止违背他们意愿的翻译作品。外文出版社的外国专家沙博理被指定为译者,他的翻译活动自始至终受到国家政府赞助人的支持和监管。例如在翻译《水浒传》的过程中,沙博理得到两位指定的中国专家的协助,分别是叶君健和汤博文。这两位中国专家不仅是沙博理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顾问,还是译作的第一位读者。他们是赞助人的代言人,也可以说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沙博理的翻译行为便受到监督和制约。可以说《水浒传》的翻译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团队合作”的成果。
尽管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沙博理作为译者的主体性受到很大制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无法发挥译者的主体性。沙博理将自己对这部小说特殊的理解阐释在译文中,译文语言反映了他本人的情感态度、文化背景和语言风格。比如广为人知的“译名之争”:起初沙博理将《水浒传》译名为Heroes of the Marsh,“heroes”用来指代小说中果敢英雄的梁山好汉。但这个译名遭到“四人帮”之首江青的不满,她认为宋江是个‘叛徒’,因为他奉皇帝诏令,率领他的部队歼灭了从东北进攻中国的辽鞑靼。又因为当时“四人帮”对周恩来总理心怀不满,又不敢明目张胆说他坏话,就拿《水浒传》大做文章,把总理比喻成新中国的宋江,借着骂宋江来把矛头指向总理。沙博理被迫将译名中的“heroes”改掉,然而他鉴于“四人帮”英语水平低,选用了“outlaws”一词作为替代。“‘outlaws’这个词在英语里是个好词, 经常用来描写象罗宾汉和他手下的好汉这一类人。这些英国中世纪有名的无法无天的人杀富济贫,直到今天仍被誉为民间英雄。”(沙博理 1984)“heroes”与“outlaws”本是两个词,精通汉语和英语两个参照系的沙博理内心明白,两者都能传达《水浒传》的“英雄”主题。他的机灵“变通”最终巧妙地抵制了翻译的“强权”。
《水浒传》原著底本众多,为翻译造成了不小的困难。最初,沙博理为了把梁山好汉及宋江之死等故事完整地介绍给读者,决定翻译100回的版本,前七十回用金圣叹的版本,后三十回用荣与堂的。大约译完五十四回时,遇到了“四人帮”言论的干涉,他们宣称金圣叹有意从原来的100回删去这些情节,目的是“隐瞒”宋江的“投降主义”。于是沙博理不得不浪费几个月的时间把译好的稿子从头至尾改得与容与堂版本一致。然而当“四人帮”倒台后,沙博理又将译稿按照金圣叹版本改了回来,又浪费了很多时间。然而他认为“为了保证文学质量,这样做是值得的”。(沙博理 1984)
作为一名翻译家,沙博理秉着对翻译艺术的忠实以及对读者的关照,尽可能地在各种机构性规约间运用灵活的翻译策略。他又自视为中国文化的忠实传播者,致力于向西方读者塑造真实完整的中国文化形象,无论内容和风格的再现上都竭力忠实原著的风貌。因此他的翻译策略以异化为主,最大程度保留中国文化。这种翻译策略在他翻译的《水浒传》的句式层面最为显著。
1. 英语意合转换汉语意合
汉语是一种意合程度较高的语言,流水句和无主句是汉语中最典型的两种意合句式,在具备语境的前提下省略主语,依靠小句之间的时间和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隐性连结句子,达到“以意统形”、“以神摄形”。(连淑能,2010:84)沙博理在翻译《水浒传》中的流水句和无主句时用到分词结构,从形式上与汉语行文风格取得对等,简洁而又传神。
【例3】只见上清宫许多道众,鸣钟击鼓,香花灯烛,幢幡宝盖,一派仙乐,都下山来迎接丹诏,直至上清宫前下马。
A procession of Taoists, beating drums and bells, playing saintly music, bearing incense and candles, banners and canopies, came down to receive the imperial envoy. (Shapiro, 2003:9)
例3原文只有一个主语“上清宫道众”,之后顶针续麻,一个接一个地紧跟5个动作。沙博理将其中三个动词转换为现在分词,作后置定语修饰主语。这样从形式上也是小句与小句相接,一环紧扣一环呈流水排布。
【例4】拿了烛台,引着大王,转入屏风背后,直到新人房前。
Holding a lighted candle, he escorted the chieftain around a screen to the door of the bridal chamber. (Shapiro, 2003: 161)
例4是汉语中典型的无主句,沙博理将增添的主语“he”置于句中,整句话由一个holding引领,使译文在形式上与原句取得了一定相似度。
沙博理对待原文“流水句”或“无主句”的转换,不仅符合英语语法规范,又保留了动词间的先后顺序,整句译句依靠语序和内在的逻辑关系凝聚起来,如行云流水,利落干脆,恰好映出汉语原句的节奏美,与原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整部译著都流露出这种简洁优美的语言风格。
2. 保留汉语语序
汉语在交代事情发生的经过时,一般按照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顺序平铺直叙。英语相对于汉语来说,语序比较灵活,状语放主句前后均可,大多数情况下习惯放于主句后。然而沙博理在处理语序问题时,常常采用“顺译法”。下面例3原句体现典型的汉语语序,译文对照原文小句顺序翻译,未作任何语序调整,平铺直叙介绍事情发展脉络。
【例5】话说故宋哲宗皇帝在时,其时去仁宗天子已远,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有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Shapiro, 2003: 261)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Zhe Zong, who ruled a long time after Ren Zong, in Bianliang the Eastern Capital, in Kaifeng Prefecture previously called Xuanwu District, there lived a young scamp named Gao.
译文顺应汉语句式的表述习惯,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先交代时间、地点、再交代人物、事件,体现出了汉人的思维特点。因为保留了源语的语言文化特征,从翻译策略上来看是一种异化法。
三、《我的父亲邓小平》(Deng Xiaoping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A Daughter Recalls the Critical Years,2002)
《我的父亲邓小平》(2000)为邓小平之女邓榕(毛毛)所著,对邓小平十年“文革”期间迭宕起伏的政治历程和悲欢离合的家庭生活作了生动的记叙和理性的思考,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背后的真相,如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判和保护,邓小平同林彪、“四人帮”的坚决斗争,邓小平对儿女的亲情和关怀,展现了一代伟人的思想、品格、气节、胸怀和胆识,以及普通人一般的儿女情怀,也记录了整个“文革”期间动荡的历史岁月与政治思想流变。著作出版之后,沙博理受毛毛委托翻译此书,译本Deng Xiaoping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A Daughter Recalls the Critical Years由外文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沙博理非常喜欢这本伟人传记,但认为西方普通读者阅读起来会有些许困难,“因为这本书介绍了极端艰难环境下中国土地上那些引人注目的人物,包括他们的历史、文化和习俗”。(Shapiro 2002:ⅱ)他认为:“我们在对外传播中一定要注意介绍我们自己最基本的情况,然后再加上我们想要说的话。要让外国受众知道我们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了解我们的文化、历史、生活和风俗习惯,也要介绍目前的新情况。”(任东升、张静 2012)在这本书的翻译中,沙博理力图再现原作中的历史事件、文化意象,同时适时浓缩,照顾读者的阅读效果,具体体现在几种文化翻译策略的运用之中。
(一)译语风格
《我的父亲邓小平》是一本涉及诸多政治性内容的“感情流水账”,逻辑清晰,感情真挚,语言通俗,平易近人,且口语化特征明显。(毛毛 2000:1)沙博理的译文“信而不死、活而不乱”,(张经浩、陈可培 2005:325)沿袭了原作风格,但相比更为简洁、凝练,抹掉了部分口语化现象,如:
【例6】费点劲儿还好说,有时还会磕碰着头。我们看着父亲这样真是心疼,可是,谁也代替不了他呀。不行,还得再想办法。还是得住到屋子外面去。(毛毛 2000:510)
That wasn’t bad, but he sometimes bumped his head. Worried, we decided to move back outside. (Shapiro,2002:428)
(二)译本序跋
译者沙博理作为《我的父亲邓小平》的第一读者,对原文获得了较为完整的感知,他充分利用译序(Translation’s Introduction)补充相关背景知识,为西方读者的阅读做了历史文化背景铺垫。
译序开篇简要介绍翻译的起因,继而点出了翻译的难点和重点:“如何诠释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动机?如何忠实再现作者的话,同时传达她的风格,她的精神?”译者从而针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给出了自己的“主观看法”,介绍了中国社会历史与共产党的诞生及发展,之后解释“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背景、性质和结果,最后表达了译者对译本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沙博理表示,“我试图忠实呈现原文,时不时加以浓缩,并尽可能传达毛毛清新的文学风格。”;“某些地方,我感到对外国读者来说不够明晰,便擅自加上了评论。这些评论以脚注形式出现。”(Shapiro 2002:iv)
(三)历史文化内容的翻译
对书中涉及的历史文化内容,包括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文化意象等,沙博理采取了文内解释和补充、文外加注,让译入语读者靠近作者和原语文化,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同时,又对原作做了适当的改写,照顾西方读者的阅读需要。
(Shapiro 2002:i)
【例7】对于刘、邓的批判,毛泽东曾想不同于彭、罗、陆、杨。(毛毛 2000:50)
Mao wanted the criticisms of Liu and Deng to be different from the criticisms of Peng Zhen, Luo Ruiqing, Lu Dingyi and Yang Shangkun.(Shapiro 2002:41)
《我的父亲邓小平》涉及众多国家领导人和老一辈的革命家,中国读者熟悉的人物在下文再次出现时作者常常只提及其姓,而沙博理考虑到西方读者对他们比较陌生,因而将姓名补全,避免读者一头雾水,不明所指。
【例8】爷爷说:“我们家里不分内外,都叫孙女,都叫爷爷。”(毛毛 2000:247)
Papa said: “In our family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she’s the baby of a daughter of of a son. She’s my granddaughter, and I’m her grandpa.”(Shapiro 2002:220)
在此,沙博理加注解释了中国社会血缘关系中的亲疏差异,再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征:
The old tradition was to call a baby born into a daughter an “outside grandchild”, and the grandfather an “outside grandpa”, in keeping with feudal male chauvinism. Only a son could continue the family line.
毛毛在译本的致谢辞中说道:“我非常感谢世界知名的中国文学翻译家、卓有成就的作家沙博理先生,他将我的作品翻译成了英文。他的精确度和速度是惊人的,并且他在译者序言和注释中提供了他本人对此书的理解。”
第四节 沙博理翻译模式及其翻译观
在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史上,根据译者的文化身份和翻译策略来分类,主要有四种翻译模式:外国译者主译,国人协助;中国译者主译,外国人协助;国人独译;外国人独译。对于沙博理而言,他的翻译模式不属于上述四种的任何一种。他的翻译模式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种新模式,我们将他称为“沙博理模式”。
翻译是一种跨越两种语言、两片文化之间的语言文化活动。一部作品的作者、译者和读者由一部译作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动态互动的三角关系。沙博理是一位具有多重文化身份的特殊译家。从小生长在美国,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他对于美国文化的理解和英语的把握自然不在话下。青年时沙博理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美满幸福的婚姻,对中国文化诚挚的热爱让他选择留在中国。五十年的翻译生涯让他对中国文化和汉语有了越来越深刻的把握,他个人的身份认同也发生了“犹太人—美国人—中国人”的动态的转变。(沙博理、宋蜀碧,1998:443)对于翻译,沙博理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翻译观”。在翻译过程中,他基于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以中国作家的视角解读原作,以英语读者的偏好呈现译语,实现了“作者——译者—读者”的“一人三体”。(任东升、张静 2011)因此,沙博理的翻译行为从作者、译者、读者三个方面体现出独特的视角。
一、忠实于原作
沙博理对于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热爱之情,他认为将中国两千年浩瀚文学翻译出版,“不仅让海外读者感受到了中国文学的魅力,同时也向世界传达着中国人的精神本质与情感——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愿望与憧憬”。(沙博理 2010)作为中国外文局的专职译者,沙博理将自己的半生奉献给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经典著作的传播事业中。他曾说:“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难度特别大。我们不仅要让外国读者明白作者的意思,还要同时能够反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味道,这样才能向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张静 2012:36)
2009年时,沙博理作为委员曾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交提案“发挥文学在文化宣传中的作用”。他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走出国门一定会大受欢迎!”(徐蕾 2009)2010年,沙博理在他的有一份提案“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中,提出了他对中国文学译介的几点意见:
(一)由外文出版社组织一个由本社专家和其他历史文化专家学者组成的委员会,专门审核我们已经翻译出版的文学书籍和期刊。
(二)选取一些优秀作品,重新编辑,使其更好地适应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的阅读习惯。
(三)加强这些图书和期刊在英语国家的出版和发行,在公关推广和广告宣传上提供支持。
二、双语能力与跨文化意识
沙博理的人生经历对其翻译理念和翻译行为产生了很多影响。他在美国度过了青年时代,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其价值观、诗学观和审美观难以摆脱美国社会的烙印。来到中国后,他接触到与美国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化,主动接近和吸收中国文化,渐渐地爱上并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他培养了英汉双语能力,熟悉了两种文化,成为一名难得的翻译专家。良好的中文功底使得他对中国文学有着很好的理解,而对于英语的精通更保障了其诠释文本的准确性。此外,他的个性和早期生活经历对其从事翻译工作也具有很大促进作用。他的热情、洒脱、冒险精神有助于他理解中国作品尤其是《水浒传》此类作品中人物的性情。他做律师的经历赋予他敏锐的感悟力和严谨的作风。最为重要的是,沙博理通过与中国妻子的结合和定居中国,实现了从身心上同中国文化的融入,正如他的真情袒露:
凤子于我不只是一个妻子,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流淌在中国和我之间的一条不断的溪流,期间流淌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社会的精髓……我爱上了凤,也爱上了龙。了解和热爱中国龙,使我更加热爱和珍视我的中国的凤。(沙博理,1998: 443)
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他的中国妻子、中国翻译家和学者为他的翻译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妻子凤子就是他的一本活字典。在翻译《水浒传》期间,外文出版社指定汤博文、叶君健做助手,“他们的英文水平、古汉语知识和辛苦的研究工作对于翻译本书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沙博理,1984: 29)。
三、读者意识
除了能够在译文中忠实地传递中国文化因素,沙博理将外国读者的反应考虑在翻译过程中。青年时在美国出生、成长接受教育的身份让沙博理深谙英语国家读者的文化储备和阅读喜好。他深知那些未曾到过中国的国外读者对于中国远远没有中国读者对他们的了解多,也更熟悉英语阅读者更偏爱怎样的语言风格。因此对于中国文学名著中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文化意象等,沙博理会采取文内解释和补充、文外加注,适当改写,甚至删去冗余的翻译策略。以此让译入语读者靠近作者和原语文化,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
综上所述,沙博理的翻译行为是一种 忠实于原作、具备双语能力和跨文化意识、注重读者反映的翻译模式。用图1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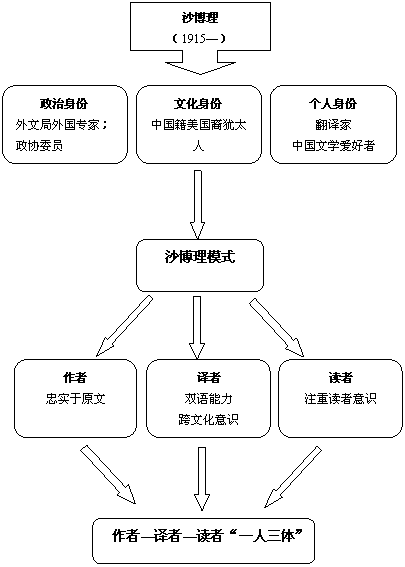
图1 沙博理模式示意
沙博理对于翻译模式有自己的见解,他赞同中西互补的翻译模式:
最好的结果似乎是一个中国人与一个外国人作为一个团体合作完成。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充分掌握两种语言,两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因此无法本能地感知一切细微差别,感受所有的共鸣,也就无法独自翻译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转引自任东升 张静 2011)
沙博理坚持在文学翻译中要内容和风格并举,不容偏废。他认为:“我们的翻译若不把内容和风格二者都表达出来,那就不算到家。”(沙博理 1991: 3)在内容的传达上,首先需要熟悉故事的历史环境,了解每个人物的个性,“切记不可逐字直译”,允许对形式稍有改动;在风格再现方面,“译者除了要透彻了解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人物的个性和特征、人物生存的自然环境,得同样透彻地熟悉外国的对等词语——或不如说外国最接近原意的近似词语”,“英语要近似中文原文的风采,或文或俗,或庄或谐,切不可二者混为一体”(沙博理,1991: 4)。
我们透过沙博理给张经浩的复信看出其翻译主张:
至于翻译准则,我基本赞同“信、达、雅”的主张。问题在于怎样做。我觉得,译者不但要精通所译文学作品相关国家的语言,了解其历史、文化、传统、习惯,而且对他本国的这一切,也要精通和了解。译文质量的高低取决于精通和了解的程度。例如,想翻译诗歌,译者自己首先就得能用母语写诗。当然,“信、达、雅”标准永远无法完全达到,但应时时朝这个方向努力。我感到我是个有明显不足的译者。(转引自张经浩、陈可培,2005: 321)
这段话透露出沙博理对中国传统译论是认同的。他不仅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充满热爱,在思想上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他接受严复的“信达雅”翻译准则,巧妙地将这一准则运用到自己的翻译实践中。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学者对沙博理译笔的评价中看出来:
沙博理的译文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概括其特质:信而不死、活而不乱。所谓“信”,是指译文在内容和风格上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作,所谓“不死”,是指译文在具体表达上则不拘一格,只要能达到翻译的目的,译者皆能视具体情况灵活运笔,大胆操控。“活而不乱”是指方法虽各有巧妙,但翻译的宗旨和目的却未有随意的变更。另外,在用语方面,沙先生的译文总的来看比较朴素、清晰、易懂易解。(张经浩、陈可培,2005: 322-323)
第五节 沙博理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文学是一种能够沟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沟的交流方式,文学翻译在这种交流中起到了桥梁作用。近年来,中国政府和学者们致力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目标,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人力财力。这方面最早的出版物有沙博理、杨宪益夫妇供职的《中国文学》英文杂志,还有后来外文出版社带头出版的“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等等。这些努力或享誉中外、或褒贬不一,但都对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沙博理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一直不间断地从事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字数近千万字,他的作品大多质量上乘,深受国外专家学者的好评,也得到了国外读者的接纳认可。他本人的翻译活动必定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有极大的指导借鉴作用。
文化身份独特、熟悉两种文化、精通两种语言、专事翻译长达五十年、译作文字达千万的沙博理的翻译,是一种新的翻译模式。他以“中国人”的文化立场解读所译中国作品,在翻译过程中以“文化间”双重身份操纵翻译,以“英语读者”的视角把握译文表达,由此实现了作者-译者-读者的“一人三体”。沙博理的翻译思想和实践特点,透视出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中国对外翻译事业的全貌,对其双重文化身份下翻译思想的研究,能够为我国翻译家研究尤其是身份特殊的“外来”译者研究提供借鉴与启示,为“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Shapiro, S. trans. Daughters and Son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56.
[2] Shapiro, S. trans. Deng Xiaoping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A Daughter Recalls the Critical Year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2.
[3] Shapiro, Sidney (trans). Outlaws of the Marsh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3.
[4] Teng Mei(滕梅). A Tentative Inquiry into Translation Policies in China since 1919 [D].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2008.
[5] 傅惠生. 《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英译文语言研究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3).
[6] 黄玉琦. 著名翻译家沙博理先生谈“我的半世中国情和对外文化传播” [N/OL]. 人民网, 2011年5月31日. 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143124/147550/14789925.html
[7] 黄子平. “灰阑”中的叙述 [M].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8] 江昊杰. 西德尼?沙博理译者行为研究:制度化翻译视角[D].中国海洋大学硕士论文.2014.
[9] 李 晶. 当代中国翻译考察(1966--1976) [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10] 连淑能. 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11] 刘彬. 勒菲弗尔操控论视野下的十七年文学翻译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4):93-97.
[12]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增订本)[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13] 毛毛.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14] 任东升、张静. 沙博理:中国当代翻译史上一位特殊翻译家 [J].东方翻译,2011(4).
[15] 任东升、张静. 试析沙博理的文化翻译观——以《我的父亲邓小平》英译本为例 [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05-109.
[16] 沙博理. 沙博理委员(美国人):让中国文化走出去 [N]. 人民日报, 2010日2月3日(20).
[17] 沙博理. 中国文学的英文翻译 [J]. 中国翻译, 1991(2): 3-4.
[18] 沙博理.《水浒传》的英译 [J]. 翻译通讯, 1984(2): 29-32.
[19] 沙博理著、宋蜀碧译. 我的中国 [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20] 田文文. 《中国文学》(英文版)(1951-1966)研究 [D]. 华侨大学.2009.
[21] 王晓燕. 新中国红色小说英译研究——以沙博理<新儿女英雄传>英译为例 [D].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22] 魏瑾. 文化介入与翻译的文本行为研究 [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23] 徐 蕾. 沙博理:94岁写提案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9年3月10日(2).
[24] 徐慎贵,耿强. 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国家实践——原中国文学出版社中文部编审徐慎贵先生访谈录 [J].东方翻译,2010(2):49-53,76.
[25] 袁静、孔厥. 新儿女英雄传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6] 张 贺.“带着理想去翻译” [N]. 人民日报, 2010年12月3日.
[27] 张经浩、陈可培.名家名论名译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28] 张静. 译者身份与译者行为——沙博理翻译模式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29] 张静. 走近著名翻译家沙博理先生 [N]. 中国海洋大学报, 2011-5-19(4).
注释
①1994中美文学交流奖 http://ias.cass.cn/show/show_mgyj.asp?id=583
②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http://www.china.com.cn/zhibo/2003-07/15/content_8784527.htm
③《鲁豫有约——一个美国人的半生中国情缘》 http://global.pptv.com/show/WZGibPKQKerhp508/pid/21701.html
④2009“国际传播终身荣誉奖”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09/09-05/1851462.shtml
⑤“中国因你而美丽”——《泊客中国》2009颁奖典礼http://ent.sina.com.cn/v/m/2009-11-16/15372771491.shtml
⑥2010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10-12/03/c_12842668.htm
⑦2011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1/03-30/2940346.shtml
